|
视觉抓取机器人 徐霞客的旅游人生,是典型的追求“所望”,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 专访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陈庆江 陈庆江(张雷 摄) 追求“所望”与脚踏实地 三联生活周刊:当我们提到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时,一个通常的认知是,在古代交通不便时他就以一位旅行家的形象踏访了大半个中国。在视仕途为正道的明朝,徐霞客是如何与旅行结缘,并以此作为一生志向的呢? 陈庆江:徐霞客很早就萌发了旅游考察的思想。从明朝前期到明朝中后期,徐霞客家是江南的大户,衣食无忧,家中甚至建有藏书楼。按照中国古代传统,他当然要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父母给徐霞客请家庭教师,教“四书五经”,但他经常在老师要求读的书下面再放上另一本,基本都是山海图经、地方掌故、轶闻奇事等,说明他小时候就喜欢各个地方的山川、人物、掌故、风情。 徐霞客曾立志表示:“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意思就是要走遍广阔天地,而非固守在一小片地方。16岁时,他象征性地参加过一次童试,没考上,就再也没参加过科举考试,这时他其实就有走入山水的想法。但两年后,父亲去世,他在家守孝,直到21岁才真正实现出游,泛舟太湖,登眺东西洞庭两山。 徐霞客旅行路线总览 (绘制 昭君) 更重要的是,徐霞客的母亲不仅没有反对,并且很认同甚至鼓励他走这条路。早年他投身山水期间母亲还健在,跟他讲,你到外边游历山川,只需要做三件事:第一,看好山水;第二,识好人;第三,回来后,把你到各个地方看到的壮美景观、风土人情、风物掌故讲给我听。这其实对他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并且,明末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旅游风气盛行,还出现了旅行家群体。从万历年间至明末,今天可考的游记著作达60种以上。当时有人说:“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也。”这实际与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多元化态势有关。比如明朝思想家李贽主张个性发展,追求自我“所望”,科学家、思想家徐光启反对空谈心性,信奉实用学问。这些观点都对当时的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徐霞客的旅游人生,其实就是典型的追求“所望”,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读《徐霞客游记》可以发现,前面部分主要是各种名山游记,后面则是他在广西、贵州和云南的游记。这些游记可以说并不好读,甚至有些枯燥。 陈庆江:是的。《徐霞客游记》可分为两大板块,包括青壮年时期写下的17篇名山游日记和晚年“西南万里遐征”的22篇游记。通常我们把徐霞客的青壮年时期,概括为“问奇于名山大川”。在他29岁到50岁这30年间,徐霞客的主要目标是游历名山大川,此时他还未能超越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模式,核心追求仍然侧重于景观审美和借山水咏志抒怀。 天台山琼台仙谷 (张雷 摄) 徐霞客所处的明朝末年,其政区划分是两京十三布政司,除南京、北京外,另设了十三个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十三个一级行政区。对徐霞客而言,他希望争取走遍两京十三布政司。在三四十岁时,徐霞客已经游历中部和东部许多省区的山川大地,便想到西南地区来,可是一直没有实现。如果读《浙游日记》,开篇有句话是“余久拟西游”,这个“西游”指的是到西南地区。1636年,徐霞客虚岁50时,说“老病将至”,如果再不出发往后就更不可能了,才终于启程前往西南地区。 1636年(崇祯九年),已经50岁的徐霞客从家乡江阴出发,一直走到云南,历时4年多。这次考察通常被人们称作“西南万里遐征”。由于几十年沉浸在山水里,随着人生积淀,这个过程中他科学考察的色彩、意味比青壮年时期浓烈得多,科考的动机、目的比较明确,方法、过程比青壮年时期更突出,成果也更丰富。并且很有意思的是,他从江苏出发,到浙江、江西、湖南,然后至广西、贵州、云南,总体上讲越往后科学考察的成分越重,活动开展得越多,成果越丰硕。到后期,他不只记录山川河流,也记录城市村庄,由点及面。应该说,晚年是徐霞客一生科学考察事业的高峰。 从整体风格、体裁上讲,《徐霞客游记》属于日记体的游记,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多见。但站在徐霞客的角度来看,他又只能这样,因为他不是偶尔出游,他每天都在路上,最后只好按日作记。从内容上讲,中国古代的游记有很多,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去关注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并如实地做详细、准确的描述。 《徐霞客游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视觉中国供图) 《徐霞客游记》确实不好读,因为里面有很多地理方位、地形地貌的信息,徐霞客虽然没有现代的测量工具,但在野外几十年的积累,使他养成了一种对地理空间的敏锐素养。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地理学家陈述彭曾对腾冲周边的火山,按照现代地理学的方法勘测,再对照《徐霞客游记》,发现徐霞客观察到位,叙述也十分精确。 三联生活周刊:该如何看待《徐霞客游记》的价值? 陈庆江:从青壮年到晚年,徐霞客几十年间投身山水,其实是把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并做到了高度统一,一个是景观审美(即观光),另一个是科学考察。他的考察包括探寻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等很多方面。比如他在广西西南部,跟当地少数民族接触、交往,写到当时土司政区的社会面貌、交通状况、边境政策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人文社会研究材料。而若从地理这个方面来讲,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一是对江河源流的考察探寻,二是对地质地貌的关注记录。 其实在他早年的名山游日记里,徐霞客就有对大小河流的源流、水文、分合等方面不同程度和角度的考察,也就是这条河流发源于哪里,流向什么地方,和哪些河流汇合,水流是湍急还是平缓,是清澈还是浑浊等问题。这种关注持续到他所涉及的各个省区,但记录最多的是广西和云南,其中云南部分又最典型。 苍山洱海(张雷 摄) 徐霞客对云南的六大水系都有涉猎,包括长江水系的金沙江段,珠江水系的上游南、北盘江,元江或者又叫红河,还有澜沧江、怒江和独龙江(也就是伊洛瓦底江)。堪称他一生江河源流考察典范的,一个是金沙江,另一个是盘江。很多人可能只读了《溯江纪源》和《盘江考》,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滇游日记》,因为《溯江纪源》和《盘江考》只是最后概括性的结论,但过程都在日记中,比较遗憾的是《滇游日记一》现在读不到了。 如果读《滇游日记二》《滇游日记三》《滇游日记四》,再结合《盘江考》可以发现,他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亲历盘江源头区域;第二顺着盘江所流经区域千里追踪,要弄清盘江的源流分合等问题;第三查阅像《大明一统志》这样的文献材料;第四访问当地人进行调查。 地质地貌这块儿,徐霞客对各方面都比较关注,最突出的是岩溶地貌,他从浙江、江西,到广西、贵州、云南都持续做了记录,对地上的峰林、峰丛,地下的溶洞等,关注很多。 被塑造的“徐霞客”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公众对于徐霞客的形象有着几重认知,大旅行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但像“地理学家”其实是个近现代的概念,历史上是如何完成对徐霞客这些形象的塑造的? 陈庆江:其实人们关注、推崇徐霞客,从他还活着的明朝末年就开始了。当时,徐霞客在文化界、政界都很有影响力。人称“闽中大师”的黄道周是徐霞客的好友,他们是莫逆之交、忘年之交。黄道周很佩服徐霞客,说他是“天下畸人”(即奇人)。文徵明的后代文震孟,是明末著名的政治人物、书法家,也是徐霞客同时代的友人,讲“徐霞客真古今第一奇人也”。还有钱谦益,他是明末清初文坛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有“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学地位。钱谦益究竟跟徐霞客有没有见过面,到现在还是一个学术公案,但他确实非常推崇徐霞客,把《徐霞客游记》介绍给书商,甚至亲自给徐霞客写传,评价“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说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就是从黄道周、钱谦益开始的。而这种推崇和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清朝,几百年间,许多文化界、学术界名人都读《徐霞客游记》,但这时对他的评价主要还是“奇人”“奇书”这个角度。 徐弘祖,号霞客(视觉中国供图) 到民国年间,他的影响力更大了,这时人们主要从地理学的角度重新认识、塑造了徐霞客。其时代背景是,从清朝晚期到民国时期,人们开始思考“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问题,要把西方的文化、科技吸纳进来为自己所用,使国家强大、复兴,像物理、数学、化学等西方学科便被引入,并与中国现实情况接轨,其中便有地理学。晚清到民国期间,许多人到西方留学,学习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回来后在中国大地上做实地考察、调研,找出救国、发展的道路。这些人都绕不开徐霞客。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徐霞客游记》,“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此以为第一部”。很多文章也都会说徐霞客是近代地理学的先驱,或者开创了近代地理学的先河,这是因为徐霞客考察山水的方法与近代地理学的一些方法和理念比较接近。比如地理学需要设计研究的目标,并运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得出地理学的观念、思想,以及与人文社会的关联等。 可以说,没有实地考察谈不上是近代地理学。像大家很熟悉的《水经注》,郦道元写作《水经注》的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坐在书斋里,通过查阅文献的方式撰写出来,而徐霞客既要读很多的书,同时几十年都在山水里。另外,虽然徐霞客没有现代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的测量工具,但几十年间在野外逐渐积累养成了对空间的一种敏锐度,他对地物的相对距离、方向的关注度和详细记载,其实跟近现代地理学有相通之处。那么这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丁文江先生。 鸡足山 (张雷 摄) 丁文江是民国地理学的一流人物。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要到西南地区做地理考察。去之前他向自己的老师请教,老师给了他一个建议,除了该有的一些准备之外,要读《徐霞客游记》。根据相关文字记载,这之前丁文江不知道徐霞客,也不知道《徐霞客游记》,但他听从老师的意见,买了《徐霞客游记》,并且带着这本书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做调查。这之后一二十年,丁文江花了大量精力研读、整理《徐霞客游记》,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丁本或丁文江本。最后他还编撰《徐霞客先生年谱》,是我们现在所知为徐霞客做年谱的第一人。因为丁文江的发掘,徐霞客被塑造成一位科学的地理学家。 到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中国东部省区的一些大学内迁,浙江大学迁往西南到贵州时,在贵州举办了一次专门针对徐霞客的学术研讨会,包括竺可桢、谭其骧、张其昀、方豪等地理学名家,都撰写了相关文章,又进一步深化了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的形象。所以在民国时期,大家关注徐霞客主要是从地理学的角度。 新中国成立后,几代国家领导人也都推崇徐霞客。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有过两次公开讲话,都提到了徐霞客,主要是推崇徐霞客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方面,甚至表示“我很想学徐霞客”。而当时由侯仁之、谭其骧、顾颉刚、黄盛璋等历史地理学界大家组编了一套《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选择《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必读书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上世纪80年代,这时对徐霞客的研究进入一个黄金时期。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的徐霞客热、徐学热,表面上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以及纪念活动和相关学术研讨会,慢慢地扩大到全国各地。这个时期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提出“徐学”一说,专门从事徐霞客研究,持续至今几十年一直在不断发展。 游圣亭,徐霞客出游处(张雷 摄)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从明清时期对徐霞客作为文坛“奇人”的看法,转向民国时期开始对徐霞客科学精神的讨论,应该说是特定时期的一种爱国主义情怀,要为地理学这门学科找到中国的一个源头?实际上,我也看到不少文章评论,因为当时地理学家们需要把徐霞客拔高到一个科学的高度,选择忽略了文本中一些不太科学的地方。 陈庆江:这种特定时期出于爱国主义情怀对他的拔高与渲染,肯定是有的。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界定,什么才是科学。“科学”是来自西方的概念。现在我们回头去看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恐怕不能说没有,但当然不能说中国古代科学跟西方科学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像西方科学一样的科学系统、科学话语、科学概念以及理论方法等。但放在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科学,孰优孰劣,得看如何思考、评述了。 另外,很多人到现在对科学的理解就是像数学、物理、化学这样可以定量分析,有规律可循,能够从理论清晰界定,再从概念上进行阐述论证,最后还可以通过实验验证的学科。那么美学、历史、政治、逻辑、伦理学呢,它们算不算科学?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术语,假设大家也认同人文社会学科也是科学,这门科学恐怕不能运用理工科的公式、定理、规律、定量等,定性地描述或许更合适。 那么,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回到《徐霞客游记》,它当然不是数学、物理、化学这样的科学,但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层面来看,面对山水地理,通过对人文社会的观察,是否得出了某种理念、某种思想,建立了一种对地理事物和人文社会的认知?所以换一个角度,应该说,《徐霞客游记》确实科学成分很多,科学色彩很浓,科学内涵很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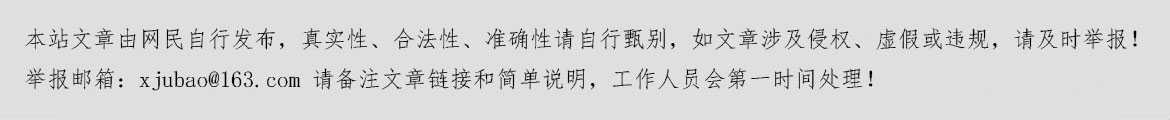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