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单单是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2016年至2017年,在单单驻校期间,我与他经常有机会在一起聊天、喝酒、谈诗。单单个子不高,一张娃娃脸,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大孩子。可这个大孩子,喝起酒来常是一醉方休,谈起诗来颇有舍我其谁的气势,写起诗来也确实有股灵气,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时有令人叫绝的构思呈现。 2017年7月初,单单离校,依依不舍地与我告别。听说他回到云南昭通不久,就被派到乡下扶贫了。由繁华的京城高校到边远的贫瘠乡村,这巨大的地域、文化的差距,我不知单单是怎样适应的;他的大孩子的性格与扶贫干部的形象,又该如何统一?我心里在暗暗地为他担心。2019年12月中旬,我到云南昭通学院参加“第九届新锐批评家高峰论坛”。在昭通三天,有两个晚上是与王单单一起度过的。此时,他正在昭通市昭阳区的一个村庄扶贫,听说我来昭通了,他白天出不来,只能晚上到宾馆来看我。这次见面,我感到他的孩子气消退了许多。他说他们村的扶贫组共有三个人,其中的党员任村支部第一书记,他具体负责上级布置下来的相关工作,周六、周日不休息,节假日也不放假,而且平时也不准请假。另一个晚上,我特意去昭通的紫光小区看望了他。他家住在14楼,房间不小,显得空荡荡的,因他扶贫长期在村里住,不常回来,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了。他说他扶贫已快两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没有忘记读书,更没有忘记他是个诗人,他不停地用诗歌把自己在扶贫工作中的点滴感悟写出来。 2020年2月23日,王单单发来诗集《花鹿坪手记》初稿,并附一信,内称:“这是我离开北京这两年写的诗歌,准备再写点后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诗集名字暂定为《花鹿坪手记》,花鹿坪是我扶贫村庄的名字。上次昭通一别,甚是挂念,遵嘱寄上拙作,以此向老师作一个我的写作汇报。”我读了这部《花鹿坪手记》的初稿,一股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灵动的构思中融入了深沉的思考,内心的热烈与外表的冷峻构成强烈的反差,我为他诗歌中的新变感到庆幸。兴奋之余,我给他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谈了我对这部诗集的看法。我建议他紧紧围绕花鹿坪扶贫这个中心选诗,把这两年写的与花鹿坪无关的诗删去。我鼓励他调动自己农村生活的积累,既要扎根花鹿坪,又要跳出花鹿坪,把花鹿坪看成是整个中国大地脱贫致富伟大变革的一个缩影。诗中所写的人物,要有客观生活的依据,但也不应是生活现象的简单实录,应当有适当的集中与概括,尤其要深入到人性的层面,折射出这个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特征。 2020年8月下旬,王单单在结束了两年的扶贫工作之后,完成了这部《花鹿坪手记》,他第一时间把诗集发给了我。当我在电脑中打开这部诗集电子版的时候,感到一种由衷的欣喜,也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部诗集比起初稿有了很大提高,更为厚重、集中、强烈,更能给人一种知性的启迪与情感的冲击。毫无疑问,这部诗集不只表明王单单诗歌创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诗坛也有着建设性意义。 王单单是农民的儿子。他出生于云南东北镇雄的一个叫官抵坎的村庄,与他扶贫的昭通农村相距不是很远。在他前些年所写的《堆父亲》《母亲的孤独》《父亲的外套》等诗作中,能看出他对故乡、亲人的深厚的感恩之情。正是出于“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自觉,他来到昭通乡下的花鹿坪扶贫时,才没有外来人的陌生感,而是很快就在村中找到了自己的父老兄弟—— 陈哑巴在贫困户信息表上/摁手印,摁不出任何指纹/我把他拇指拿起来看/泥巴敷了一层。我没有/让他洗掉。我默认/这泥斑,就是他的指纹/这里面藏着他的命(《花鹿坪手记》) 这勤劳的老实巴交的村民,不也一样生活在他的故乡官抵坎吗? 他置身于花鹿坪村民之中,像在自己家乡一样。他的《花鹿坪手记》,再现了贫困农村在扶贫攻坚中的深刻变革,洋溢着血浓于水的真情,袒露着他对花鹿坪人的深切关怀与大爱。王单单为花鹿坪村民身上闪烁的美德、为他们的点滴进步感到自豪与骄傲,也为他们的某些惰性、愚昧感到焦急与羞愧。他在《激发帖》中训斥懒汉,在《融化记》中苦口婆心地劝说不砌牛圈的养牛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他劝阻了要嫁闺女的村民办喜宴,制止了刚从湖北回来重点隔离村民的麻将牌局……这不只是扶贫工作队员的职责,更是面对最贴心的人才会做出的关爱的举动。诗人的确是将自己生命里的爱和痛都倾注到诗歌当中了。 在两年的扶贫工作中,王单单与他的扶贫战友一起共同奋战,花鹿坪村所有贫困户均已脱贫出列。而对诗人王单单来说,在圆满地完成了扶贫任务的同时,更使他对自己的人生和诗歌创作,有了深一层的感悟。他说:“我写花鹿坪扶贫系列诗歌,是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两年,我不是去体验生活,而那就是我的生活本身,许多素材早已烂熟于胸中,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个主题在呼唤我的写作,而不是我要为了完成这个主题去写作,二者区别很大,关乎心灵的活跃与抒写的自由。”这段话说得非常好。毋庸讳言,当诗坛上充斥着大量苍白的、缺血的平庸之作的时候,当“同质化”成为当下诗歌脱不开的创作魔咒的时候,当诸多年轻诗人为找不到突破的门径而苦闷的时候,听听王单单这段发自内心的感言,投身到社会大变革的实践中去,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无疑是有普遍意义的。 乡愁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诗人永远摆脱不开的情结,王单单也是一位怀有浓郁乡愁的诗人。他说:“在故乡,只要大声说话,隔着山丘与丛林,村里人都能辨别出我的声音。我希望在诗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村庄,我希望站在村口喊一声,人们就知道是我回来了。”这些年来,王单单通过诗歌创作,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村庄。感谢扶贫生活,给了他一个历史的机遇,让他的生命、让他的故乡与花鹿坪融合起来,对他来说,花鹿坪不再是一个地名,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成了凝聚着他的生命、他的成长、他的意志、他的情感的诗的家园,成为他安置乡愁的精神原乡。对王单单来说,这才是他参加花鹿坪扶贫并写出《花鹿坪手记》这部诗集的意义所在。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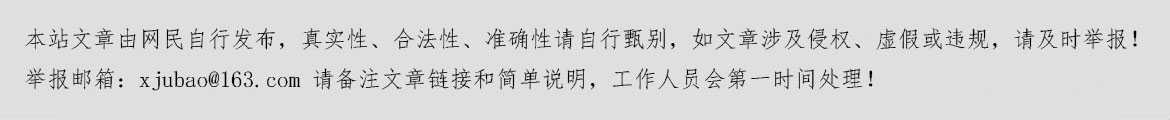
|